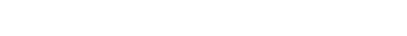《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述评 |
|
| 发布时间:2012-6-20 来源:admin 阅读次数:6042 | |
|
王 素 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是作者近十余年利用敦煌、吐鲁番及甘肃、新疆其他地区出土文书研究唐代西域史的成果结集。所收各文,都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有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的大改,材料的增补和见解的更新,都与原创性研究相差无几。前十一篇以唐西州为主,后五篇兼及唐代的安西、北庭、龟兹、敦煌,因而统称为唐代西域史研究,大致名实相符。这些论文的内容,有的各自独立,有的彼此相关,涉及唐代西域史的方方面面。 《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原是作者2008年发表的新作,此次收入本书又有所修订,足见作者治学之精益求精。我们知道,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在其地先后设西昌州—西州,治高昌城,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又设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具体负责经营西域事务。直到高宗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迁治龟兹,都护府与州府同在西州办公,时间长达将近二十年。关于二者的关系,此前研究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有的问题虽然已经解决,但有的问题还未达成共识。本文通过对传世文献的考辨,以及对大量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分析,认为唐灭高昌设西州,由于政策的需要,最初置西州刺史与安西都护,是分别用人的。首任西州刺史为谢叔方,治高昌城;首任安西都护为乔师望,治交河城。前者治民,后者治军,形成州府与都护府两套机构和人马,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分治管理体制。然而,这种管理体制并不利于西州的统一管理,也不能很好地应付复杂多变的西域形势。特别是贞观十五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势力扩大,对西域构成极大威胁,引起朝廷对西州管理体制的反思。于是,贞观十六年九月,朝廷以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将都护府治从交河迁至高昌,与原州府合二为一,由都护府统管州府事务,实施一元化的军政管理。此后,柴哲威、麴智湛二人相继以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情况相同。直到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西迁龟兹,才改为西州都督兼西州刺史,由西州都督府统一管理西州军政事务。这些见解,对于深入了解西州在西域的地位,以及唐王朝对西州—西域的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是一篇后来居上带有总结意味的论文。关于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前人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墓志,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要想“发人所未发”,就必须更加注意细节,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披露的信息汲取到极致。本文认为:唐于贞观十四年灭高昌、设西州,为了削弱高昌旧有势力,加强对西州的控制,把高昌王室及大族、百姓等不少人迁移到长安、洛阳。为了补充西州的人力,又一方面向西州发遣罪犯,一方面有计划地把雍州无地或少地的民户迁来西州。高宗即位后,由于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叛,导致西域政局不稳,为了稳定政局,又把高昌王室及大族等一干人马放还西州。但由于西州土地毕竟有限,不能容纳过多的人口,于是,大约龙朔、总章间,又有计划地把西州拥有土地的一些民户迁出西州,而重点是昭武九姓粟特人。这些见解,不少为首次提出,值得关注。其中,关于昭武九姓粟特人的迁移,尤其令人瞩目。本文认为:西州粟特人居住的崇化乡时间较早,沙州粟特人居住的从化乡时间较晚,存在前者迁移到后者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大胆且有意义的假设。 《吐鲁番所出〈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及其相关文书》是一篇典型的“以小见大”的论文。池田温先生早年曾根据大谷2831、1013、1037、1254、1419、1256等号文书断片,拼合整理为一组三件残文书,定名为《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这件辩辞后来还曾经过不少研究者的探讨。但本文感觉仍有“未发之覆”。本文将这件辩辞置于贞观十六年西突厥围攻西州天山县的背景下,旁征博引,条分缕析,重新定名为《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六月安西都护府户曹勘问延陀行踪案卷》,并根据其他相关文书,揭示出案卷的背景及内容:贞观十六年九月,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将都护府治从交河迁至高昌,经过击退西突厥入侵,解天山县之围,“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处密之众而归”等一连串军事行动,使西州得到稳定。然后于贞观十七年六月,令安西都护府户曹在西州展开一系列的户口清理、调查工作。并认为:该案卷反映出安西都护府对西州进行全面管理的实态。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是一篇独具只眼的论文。学术界一般认为:史载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四月,由于吐蕃大举入侵西域,唐朝被迫罢弃安西四镇,值得相信,此后安西都护府应该撤回西州。少数研究者虽有不同看法,但由于缺乏坚实材料佐证,很难改变这个结论。本文则先根据吐鲁番文书披露的信息,力证咸亨二、三年间,龟兹仍称安西,并有不少西州人在安西活动,咸亨三年至上元三年(676),西州都督府建制一直存在,安西都护府并未撤回西州;然后根据敦煌、吐鲁番及其他相关文献,对高宗龙朔二年(662)至总章二年(669)西域政局进行细致分析,得出的新结论,即唐虽于咸亨元年被迫下令罢安西四镇,但实际罢弃的只是于阗、疏勒二镇,龟兹、焉耆二镇仍在唐手,并未放弃。 《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都司”考》大致属于姊妹篇。前文谈到的“陇右诸军州大使”,兼统西域军政;后文谈到的“都司”,即为“陇右诸军州大使”、“碛西节度大使”等下属具体管理西北军政、西域军政的非常设机关。两文对“都司”的沿革和职掌,“陇右诸军州大使”、“碛西节度大使”等兼统西北军政、西域军政的具体事例,均论之甚详,可以采信。 《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与《唐代龟兹白寺城初考》也大致属于姊妹篇。1941年,张大千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获得唐张君义文书四件:一件为景云二年(711)勋告,一件为乘驿马牒文,两件为景龙三年(709)公验。后文是对第一件公验提到的“白寺城”进行专门的考证,认为该城即今库车西面玉其土尔遗址。前文是以第一件公验提到的“白寺城”为切入点,对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的变化,特别是突骑施娑葛包围安西的原委,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认为,据张君义文书,君义属于四鎮经略使周以悌的前军,参加了包括安西在内的龟兹—焉耆一带针对突骑施的两次战斗:第一次在景龙三年五月六日至十四日,经历了连山阵、临崖阵、白寺城阵、仏陁城阵、河曲阵、故城阵、临桥阵等十一次战阵;第二次在同年六月某日至二十五日,经历了城北某阵、城西莲花寺东涧阵等战阵,并最终取得胜利。突骑施娑葛于景龙三年七月遣使向唐投降,唐封娑葛为归化可汗。还对此役之后,唐对西域原有边防体制及民族政策进行调整等情况,进行了宏观论述。 《跋吐鲁番鄯善县所出〈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以《献之牒稿》的录文、定名及年代等方面的考证入手,进而对《献之牒稿》披露的阿史那献可汗与开元元年(713)或二年始建的定远道行军的来龙去脉,以及与此相关的开元七年请居碎叶的“十姓可汗”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认为:这件《献之牒稿》的准确时间应在开元九年末。定远道行军的任务最初是征讨十姓部落酋长都担,后来变成与北庭唐军联手,移屯天山东部的伊州甘露川,负责防御东突厥。开元七年请居碎叶的“十姓可汗”应为阿史那献可汗。 《唐代西州天山军的成立》认为,唐在西域置“军”,四鎮的镇守军除外,时间明确的,还有武周长安二年(702)的庭州烛龙军(长安三年改名瀚海军),中宗景龙四年(710)的伊州伊吾军。至于西州天山军,时间不详,有贞观十四年、开元二年、开元中三说,开元二年说几成定论。但实际可以商榷。本文先根据开元十年始撰、开元二十六年成书的《唐六典》提到伊吾、瀚海二军,没有提到天山军;吐鲁番出土开元十年左右西州都督府牒也没有提到天山军,认为开元十年左右天山军仍未设置。然后通过考辨,认为天山军很有可能是开元十五年之后不久设置的,与开元十四年闰九月吐蕃与突骑施联手入侵西域有关。最后认为,史籍所以误为开元二年,是因为天山军有可能是在开元二年设置的定远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史籍有关天山军始置于开元二年的记载,实际上是定远军的始置时间。 《对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的探讨》指出,所谓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专指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获得的一批文书残片。对于这批文书残片,前人虽已进行过整理和考释,但释文和解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先将这批文书残片析为三组,第一组定名为“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高昌县访捉逃兵刘德才、任顺儿、梁日新案卷”,第二组定名为“唐天宝二年前后交河郡高昌县访捉碛西逃兵樊游俊案卷”,第三组定名为“唐天宝二年前后交河郡高昌县访捉逃兵未获文书”,然后根据其他相关大谷文书残片,分组进行包括释文、内容在内的考订,纠正了原释文的一些错误,对产生逃兵的原因也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解说。 还有五篇考据论文,即:《唐代西州的突厥人》,除了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还利用了雅尔湖千佛洞、伯孜克里克千佛洞残存的突厥文题记和突厥装供养人像,对唐代在西州定居的突厥人的来源及其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除了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还利用库车出土文书,对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库车出土唐安西官府事目历考释》的主要内容已见于《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唐代安西、北庭两任都护考补——以出土文书为中心》通过考证为唐代安西、北庭增补了两任都护:一为高宗上元三年安西某都护,一为玄宗开元十五至二十一年间北庭阴某都护。《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赞同池田温先生之说,将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定为永泰二年五月。 当然,本书所收论文,也难免存在些许问题。小的问题可以不论。如第177页注①说“荣新江评介文载《唐研究》第五卷……第332-336页”,其中之“《唐研究》”应作“《敦煌吐鲁番研究》”,“336页”应作“337页”。大的问题希望将来能够改进。如第100页说:“娄师德于圣历元年(698年)、二年两年间两度出任陇右诸军大使,说明此职最初并非常设的使职。”但此说可能存在问题。娄师德于圣历元年、二年两年间两度出任陇右诸军大使,仅见《新唐书·武后纪》:圣历元年四月“辛丑,娄师德为陇右诸军大使,检校河西营田事”。圣历二年“四月壬辰,魏元忠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总管,娄师德副之,以备突厥。辛丑,娄师德为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连续两年都在四月辛丑这天被任命为陇右诸军大使,是否太过巧合?本身就值得怀疑。而两《唐书·娄师德传》及《册府元龟》均仅记第一次。《资治通鉴》卷二○六稍作处理,作:圣历元年四月“辛丑,以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营田事”。圣历二年四月“壬辰,以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充天兵军大总管,以备突厥。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怀抚吐蕃降者。”我以为《资治通鉴》的处理是正确的,即圣历二年娄师德是改任天兵军副大总管,同时仍兼陇右诸军大使,并非再度出任陇右诸军大使。 此外,所收文章也还有可以精益求精之处。如《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都司”考》所说“陇右诸军州大使”兼统西域军政,其实本是汉晋以来凉州刺史代理西域故事。《晋书·地理志上》凉州条即云:“魏时复分(雍州)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再如《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谈到最初安西都护与西州刺史分别用人和分治交河、高昌二城,恐怕也含有类似清代“督、抚不同城”的因素。清代督、抚品级相近,职掌相关,容易引起矛盾,故有“督、抚不同城”之说。《清史稿·圣祖纪三》康熙五十一年六月丁巳条云:“命穆和伦、张廷枢覆按江南督、抚互讦案。”可见当时督、抚争斗之烈。同书卷四三八《林绍年传》记绍年曾“疏言督、抚同城任事非便”,同书卷四四六《郭嵩焘传》记嵩焘曾慨叹“事皆繇督、抚同城所误”,可以参阅。这二例说明,典章制度的研究,不仅需要追源泝端,还需要溯流竟委。 综观上述,可以认为,本书总体上是经得住严格检验的。安志君的论文有三大特点:一是学术史的梳理十分清楚。这一方面是因为训练有素,很多年前安志君就撰写过《近年来曹操评价问题讨论综述》(《历史教学》1987年第6期)和《建国以来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1期)一类学术史回顾文章;另一方面是因为其生也晚,所研究的问题,大多已有很多学术史的积累,不进行清楚的梳理,就不知道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二是“二重证据法”的运用非常娴熟。这主要是因为作者近十余年撰写的论文,如王国维先生所说,都是需要以“纸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新材料”(出土文献)互为证据的论文。如果不能娴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要想在前人爬梳无数遍的有如断烂朝报的故纸堆中寻找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线索,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而能够娴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效果自应大不相同。作者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的高手,故本书所收论文,考论大都理据皎然,结论大都令人信服。三是武大唐门的学风贯穿始终。这一点最为重要。武大唐门的学风,是以实证史学为基础的。实证史学的要义之一,是强调应首先打好扎实的传世文献功底,然后再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或结合出土文献进行历史研究。我当年向唐长孺先生求学,硕士三年(1978-1981年),唐先生就只要求我专心通览传世文献,不要考虑写文章发表,也不要过早接触出土文献(当时主要指敦煌吐鲁番文书)。安志君在武大唐门的求学之路,与我应该是相同的。也正因如此,本书所收论文,每一篇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作者扎实的传世文献功底,以及得心应手的驾驭出土文献的能力。我们相信,安志君一定能够全面、完整地继承唐门衣钵,将唐长孺先生倡导并实践的实证史学的学风进一步发扬光大!
(作者王素,1953年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