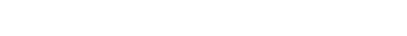王素:揭秘地下“中国通史” |
|
| 发布时间:2015-12-18 来源:admin 阅读次数:111671 | |
|
继整理和研究文书、墓志、简牍之后,王素致力于世界现存最 后一批甲骨文宝藏的整理,他要让《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 系列丛书,成为未来最好的甲骨文整理研究著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苗苗 《瞭望》新闻周刊2015年第49期(总第1657期)“人物”专栏 2015年12月7日出版
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目录中有一项常规栏目叫“课题项目·重大项目追踪”,关注的是故宫博物院也是文博系统少有的国家级重大项目的进展情况,包含“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保护与整理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项目”。 这些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指向同一个人——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王素。如果加上他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级出土文献整理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王素涉猎的出土文献门类已经达到四个——文书、简帛、墓志、甲骨,占了出土文献五大门类之四(还有一个是金文),是业内唯一一位整理和研究出土文献门类最多的学者。 与传世文献有可能因种种原因被修饰和篡改不同,出土文献是真实反映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保存了大量传世文献所没有的新资料,具有证史之实、纠史之误、补史之阙等重要价值。 然而,对普通人而言,不仅难以接触到出土文献原件,而且难以读懂其携带的文化密码。作为整理和研究出土文献的历史学者,王素一马当先,成为最先揭开这些文献秘密的人。
发掘“历史碎片”的内涵
今天,人们可以在国家图书馆轻易查阅到王素整理的出土文献著作,几乎都获了国家权威机构颁发的大奖。这些著作详细记录着文献出土时的原始信息,包括图片,以及被隶定过的文字(将古文字按照原有结构转化成现在通行的繁体字)。但是人们很难想象这些出土文献整理背后的故事。
2015 年6 月, 王素在长沙简牍博物馆整理三国吴简
回忆整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时,王素负责的《竹简》第一卷和第三卷属于“采集简”,即后来被发现已经因施工而招致扰乱的竹简,不仅大部分失去了相互关联的原始状态,而且得以保留原始状态的少部分也变得残缺不全,上面仅留下淡墨残笔。 王素和随同整理的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吃力地记录着、释读着,每天傍晚从工作地点返回住所已经是筋疲力竭。他要按照考古清理的操作要领,结合揭剥技巧,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尽量按其现存状况、叠压的层次,分层,分面,细心地进行揭剥清理和记录,把竹简的层位、序列、数量、转折面等都要记录下来。整理工作完成后,王素笑着感慨:“生亦何欢,死亦何惧?”而他的眼镜度数也在此期间迅速攀升至1000度以上。 “我们就想尽最大努力辨认,恨不得把每个字都释读出来。”王素说,“今人研究三国史,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三国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数量巨大,仅有字简就近8万枚,可望极大地改变三国史史料贫乏的现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相较“采集简”上的模糊字样,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新中国出土墓志的字迹要清晰得多,但是吐鲁番出土文书由于出土地在晋唐时期属于边疆,和中原文字存有一定差异,加上很多文书中还掺杂了大量俗别字(官方文字以外民间撰写的文字),而新中国出土墓志中也不乏很多今天看来十分不规范的文字,需要逐一“翻译”成今天通行的文字,这些都给王素的整理工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然而,对有着过硬识别古文字能力的王素而言,释文还不是最难的,真正考验他的是如何深入发掘这些已是历史碎片的出土文献内涵。 2014年12月,应著名史学刊物《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辑)》约稿,王素把历时两年三个月写成的一篇三万字长文——《唐麴建泰墓志与高昌“义和政变”家族》交其刊登发表。这是王素近些年自认为最满意的文章,他通过重新剪接组装河南孟津新近出土的唐麴建泰墓志,以及吐鲁番出土文书和传世文献中的相关线索,将高昌“义和政变”家族与唐王朝平定高昌、治理西州的谋略,置于隋唐之际中原王朝与西域民族关系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得出了与其他公开发表论文截然不同的结论,填补了高昌末年和唐朝初年的整个西域史研究的空白。 这次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也让他体会到,对于史家,尤其是实证史家而言,历史研究就像拼图,需要研究者用心拼接已成碎片的史料,只为尽可能拼成一幅大致完整的图像,还原历史真相。 他常说,整理出土文献,若没有出土文献之外的传世文献或曰通史功底,就很难从中发现问题。而做出土文献研究,若没有整理出土文献的经历,就会使研究陷入盲人摸象、以管窥豹的局限。只有整理与研究相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其成果才能既有细节,又有大局观和大视野,也就是常说的“通识”。 炼就中国通史功底 出土文献整理的几个国家级重大项目落在王素肩上,不纯属机遇,更多的是非他莫属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978年,王素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唐长孺教授,研习汉唐历史。唐长孺还兼任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并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工作。1981年王素毕业前夕,唐长孺就对他说,“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工作非常繁琐,需要心静而且坐得住的人来做。你比较合适。”这句话和随之而来的毕业分配,决定了王素初出校园就与出土文献整理和研究结缘了。就这样,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释文进行核校,经他过目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原件多达3000余件。 1991年,全10册《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刚刚全部出版,还在担任同书图文对照本责任编辑的王素,突然又接到一项新任务。原来已经运作了8年的另一项国家级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因负责人被调离无人继续接任,而一度陷入停顿。为此,牵头该项目的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领导找到王素,对他说:“在古文献研究室,谈到中国通史和传统文化的基本功,没有人比得上你,这个项目只有你能接手,希望你能承担起来。”就这样,王素担起了《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编审和出版工作。 《新中国出土墓志》计划出书30卷,60册,被学术界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部墓志丛书,该书收录的墓志,年代自秦汉到中华民国,内容涉及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非具备综合的通史型传统文化知识的人是不能胜任的。 如今,第一期成果——10卷、19册《新中国出土墓志》整齐地摆在王素的书架上,见证着曾经的付出。第二期工程的第一卷也刚刚出版。看着这些沉甸甸的书籍,王素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他告诉本刊记者,他的父亲生于书香门第,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深信文学素养需要“家学”。早在他6岁时,父亲就要求并训练子女们背诵诗词和古文。一首七言绝句,读一遍必须做到背诵,一首七律,读两遍必须达到背诵。年幼的他因为每次都能达到父亲要求,而成为父亲重点培养的“孺子”。到24岁考大学前,他已经能够背诵诗词近4000首、古文近400篇。 “父亲常对我说:‘学问之道,首先要打好基础,基础越广博,越深厚越好。要抓紧时间博闻强记。以后你就会知道:由博返约易,由约向博难。’”王素回忆道。 1966年文革开始,刚满13岁的王素小学毕业,正常的学业进展受到中断。但此后直至恢复高考前,他在父亲教导下,系统阅读了各类文史典籍。王素说,他父亲曾任湖北省工农速成中学(今华中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前身)图书馆管理员,有条件为他提供各类书籍。他记得,1969年之后,他被下放到湖北荆门和嘉鱼劳动的5年半时间,每次回城里老家探亲后返乡时,身上挑着的全是父亲为他备好的两筐各类文史典籍。24岁前,他已经通读了《十三经》《二十五史》《全通鉴》《百子全书》《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等重要文史典籍。 早期打下的古典文史功底,使他在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成为第一届大学生,并在半年后参加了被社会上称为“黄埔一期”的研究生考试,以高分被录取,成为唐长孺的门下高足。 挖掘甲骨文最后宝藏 已故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曾统计,故宫博物院藏有22463片殷墟甲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批甲骨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13年11月中旬,王素牵头第一次进入故宫博物院地库调研院藏甲骨工作之后,这批甲骨才重新面世。故宫院藏殷墟甲骨22463片左右,数量可能较胡厚宣的统计稍有增减,约占世界现存殷墟甲骨总数的18%,仅次于国家图书馆(34512片)和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25836片),位列世界第三。消息传出,学界哗然。 如何让世界现存的这最后一批甲骨文宝藏得到更好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大事,也成为新成立的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的头等大事。 2014年2月25日,故宫博物院对外公布“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项目正式启动。王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甲骨文整理比较难,因为甲骨容易破损,我们计划尽快推动这个项目在国家立项,大约5年可以完成。不仅要数清楚院藏甲骨文的总数,更要弄明白这些甲骨文写了些什么。” 甲骨文是王素继整理和研究文书、墓志、简牍之后,负责的出土文献新门类。2015年4月1日,故宫博物院召开对该重大项目的开题论证会,国内甲骨文权威专家悉数到场,为整理和研究这批甲骨建言献策。 王素坦言,由于故宫博物院甲骨文整理研究人才相对缺乏,急需通过“请进来”的方式,集结优势研究力量。为了项目顺利推进,他们目前已经成立了五个组——释文组、编目组、摄影组、拓片组、摹文组,其人员构成要么是故宫博物院内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要么是外聘的专业一流技师。未来的甲骨释文还会特邀院外专家学者参与解读。 王素充满信心,他要让最后的成果——《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系列丛书,成为未来最好的甲骨文整理研究著作,所收甲骨,不仅有正、反、侧三面的原物、拓本、摹文图版,还要采用全彩版印刷,尽可能全方位留存这批甲骨文的信息资料。 他坚持认为,对这批甲骨文的整理,也要按照出土文献整理的最高原则——最大可能完整保存原件披露的一切有价值的信息。□
|
|